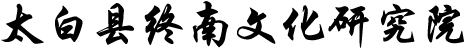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遭遇过多种恶性传染病,给人们带来的苦痛罄竹难书。瘟疫不曾远离人类,并多次出现在作家笔下。瘟疫席卷而来,个人小小的抉择就可能事关生死。
在一个个试炼人性的故事中,作家通过斑驳的历史进程中人类或无助或无畏、或恐惧或逃避的态度,展现了人性的韧性与脆弱、光明与阴暗。读者会看到,危机并不遥远,只有反思人类的行为,才能让健忘的记忆增强点生命力。

在很多早期的文学作品中,瘟疫只是一个故事元素。例如,意大利作家乔万尼·薄伽丘写于14世纪的小说《十日谈》,讲述了1348年佛罗伦萨发生的一场可怖的瘟疫,有的人清心寡欲、有的人纵情欢乐、有的人态度折中、有的人逃走躲避……七女三男在乡间别墅的10天里讲述了100个故事,瘟疫则构成了故事发生的背景色。
在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写于1595年的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约翰神父说:“我在临走的时候,因为要找寻一个同伴,去看一个同门的师弟,他正在这城里访问病人,不料给本地巡逻的人看见了,疑心我们走进了一家染着瘟疫的人家,把门封锁住了,不让我们出来……我没法子把它送出去,现在我又把它带回来了;因为他们害怕瘟疫传染,也没有人愿意把它送还给你。”维洛那出现瘟疫并被封锁,使得送信的约翰神父无法把朱丽叶假装去世的消息告诉罗密欧,才导致出现最尖锐的戏剧冲突——罗密欧、朱丽叶先后自杀。
文学作品中第一次全面展现瘟疫,要等到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在1722年出版的小说《瘟疫年纪事》。这部基于1664年伦敦瘟疫写出的作品,描写细致、手法别致,小说中还附上了伤亡统计、政府公告等,包括《有关被传染房屋及罹患瘟疫人员的规定》《为使街道净化并保持芳香的规定》《有关闲散人员和无故集会的规定》等。这本受到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澳大利亚作家库切等当代文坛大家推崇的作品,影响了《霍乱时期的爱情》等作品的创作。

在人们对疫病不了解的时候,甚至会把病症当成美的表现,例如肺结核导致患者脸色泛红而受人青睐,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文学作品。在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中,玛格丽特得了肺结核还门庭若市。法国诗人兰波还写出了诗句:“I,殷红,喋血,美人/嗔怪和醉酒时朱唇上浮动的笑意。”我们应该看到,肺结核患者众多、危害严重,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丽姬娅》中的丽姬娅、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的海伦、日本作家德富芦花的《不如归》中的浪子等都死于肺结核。
死亡并不可怕,很多人敢于直面疫病,甚至甘愿献出生命。在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写于1912年的小说《死于威尼斯》中,阿申巴赫得知霍乱在威尼斯蔓延后并没有离开,而是留下来,跟着塔德乔的足迹在疫区游走,结果感染霍乱而死。在法国作家莫里亚克于1922年出版的小说《给麻风病人的吻》中,让·佩罗埃尔故意染上麻风病而死,希望妻子诺埃米从婚姻中得到解脱。

人们该如何面对疫病呢?法国作家加缪写于1947年出版的小说《鼠疫》中,描写了人们面对鼠疫不同的状态。省府不想公开信息,里厄医生说:“你们管它叫鼠疫也罢,发育热也罢,关系不大……现在的问题不是推敲字眼,而是争取时间。”疫情发生后,电影院里重放多遍的电影仍然有观众,影院不会减少收入,毕竟人们还需要文化生活。一些人则开始逆来顺受、寻欢作乐,参加祈祷的人少了,参加迷信活动的人却增加了。记者朗贝尔一开始想逃走,可是他在能逃离的情况下还是主动留下来了,在荒诞的世界中展现出人的坚守。里厄认为:“这一切不是为了搞英雄主义,而是实事求是。这种想法可能令人发笑,但是同鼠疫作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实事求是。”抛弃幻想、理性等待,里厄在荒诞的世界中抬起抗争的头。在人们的共同努力下虽然迎来了胜利,但突然停止的疫情还是让人深感茫然。
这种责任感也体现在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于1995年出版的小说《失明症漫记》中,同时让人们看到了“在别人失明的情况下尽有眼睛的人的责任”的艰难。很多人突然失明,社会失序,人性泯灭,连教堂中神灵的眼睛也被蒙上了白布。失明的人被关进精神病院,世界发生了从相亲相爱的盲人世界到严酷无情的盲人王国的变化。医生的妻子作为见证者,目睹了人性的脆弱,仍无私地帮助身边的盲人,让大家慢慢找回丧失的人性和尊严,并带领大家从精神病院回到了家中。吊诡的是,当大家复明后,她却失明了……
疫病让人在追问中看清历史,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把荒诞的世界、扭曲的人性浓缩到了1970年出版的小说《癌症楼》的病房中,科斯托格洛托夫治愈癌症、获得新生的奇迹,源自索尔仁尼琴的亲身经历。
疫病还会拉近彼此心灵的距离,马尔克斯于1985年出版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就让人看到了苦难中的相濡以沫。英国作家维多利亚·希斯洛普出版于2005年的小说《岛》,通过阿丽克西斯的追问,把佩特基斯家族几代人与麻风病的抗争史展现在读者面前。

我国的很多小说中也提到了疫病,瘟疫之后的人祸才是作家关注的焦点,例如《水浒传》开篇的“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就是这样。从《红楼梦》中林黛玉咳血到鲁迅《药》中的人血馒头,再从陈忠实《白鹿原》中小娥死后的瘟疫到毕淑敏《花冠病毒》中对“非典”的艺术反思,作家一直对疫病持审视的态度。在阎连科1998年出版的小说《日光流年》中,三姓村的人被活不过40岁的魔咒所束缚,活到40岁的村民会得一种叫吼头症的绝症。四任村长想了四个办法,多多生育、种植油菜、翻地换土、开渠引水,但并未带领村民走出命运的怪圈。他们是西西弗式的英雄,这个讲了四遍的故事还将被继续讲下去。
在每本小说的结尾,疫情总会结束,也总有人会活下来,让讲述成为责任。瘟疫是人类的灾难,而同时疾病成为作家思考某些社会问题的载体,作家在写作中更多关注的是对人性的批判,在反诘中思考褪色的记忆、探寻社会的走向。例如,英国作家狄更斯在1857年出版的小说《小杜丽》中,有一章的标题是“流行病的蔓延”,批判的其实是人们对股市的追捧。
瘟疫作为看不见的威胁,是死亡的近邻,人们在不安中的所思所做,更能看出人性的成色,对于幸福的追求、生存价值的思考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如果把人生看做死亡的延宕、趋死的过程,对死亡的关注则激发人们思考、谋划人生。正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所说:“自从死神灼热的一吻,便须为苦难而热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