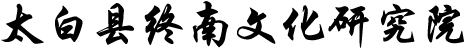宋代笔记数量多,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唯宋则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谭,所述皆平生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流。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阙”,大抵道出了宋代笔记的特点和价值。宋代士人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别具才学识见、胸怀气度与人格品味,同时谐趣幽默,笔记正是能更好地载录文人思想、性情、生活的文体。宋代笔记作者常以亲闻亲见的资料来源,记录日常生活,品藻身边人物,抒写生活情趣,其在反映社会生活和人生境遇的广阔性、真实性特别是谐趣性上,超越了同时期的其他文体样式和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笔记作品。宋代文人的谐趣逸事,在宋代笔记中有充分的记载,显现了宋代文人特有的机智敏锐与生存智慧,同时也影响了宋代笔记的风格特征。
宋代文人在人际交往中,同僚、门人、文友谈笑打趣,调和人际关系,增进相互了解,也是文人间竞才斗志的方式。如苏轼与刘攽,交往甚厚,缘于政治见解的相近,学术观念的相近,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滑稽善谑的性格相近。元祐初期被召还的刘攽与苏轼同为馆职,宋代笔记中记载了两人文字往返、斗智谐趣之逸事。如《曲洧旧闻》所载人之熟知的“皛饭”与“毳饭”,“滑稽辨捷为近世之冠”的刘攽竟然也笑之捧腹,“知君必报东门之役,然虑不及此”。这是宋代文人社交生活中以文字游戏之法斗智斗趣的常见方式。
宋代文人以特有的谐趣幽默个性,显现了积极乐观、旷达超逸的风姿气度,同时谈笑嘲谑也多指向自我。如《谈苑》所载“曼卿坠地”,驭者失鞍,马惊坠地,对于临街出行的官员而言,是尴尬至极、有失颜面的突发事件,而石延年却能找到最好的自我解嘲方式:“从吏遽扶掖升鞍”,慌乱的场景中延年仍能喜笑颜开、自我打趣:“赖我石学士,若瓦学士,岂不破。”这种机变调笑之语,更能见出其机智敏锐、心性豁达的一面。《春渚纪闻》所载“和贼诗”与“避孔子塔”,“虽得大风恶疾,而乘机决发,亦不能忍也”的刘攽,调笑戏谑的性格丝毫未改,以苏轼“乌台诗案”为谑,影射与之诗文唱和为“和贼诗”,往往难逃“狼狈而归”的下场。苏轼反谑尤甚,以刘攽身遭恶疾调笑谈谑,“避孔子塔”,戏谑“鬓眉皆落,鼻梁且断”的刘攽。这是深度默契后的心心相惜、患难与共后的豁达明朗。
宋代文人谐谑幽默,也为宋代文艺思想的滋生平添了轻松愉快的氛围。苏轼与同僚、朋友、学生论辩酬唱,间以谈谑,最具代表性。《齐东野语》载:“王祈尝语东坡曰:‘我有竹诗两句最得意。’诵云:‘叶垂千口剑,竿挺万条枪。’东坡笑曰:好则虽好,只是十条竿,一个叶儿。令人忍俊不禁。”诗书兼善的苏轼以此来谐谑王祈“最得意”之状,同时也表明夸张也要以生活常识为基础。《独醒杂志》所载关于苏轼与黄庭坚的相互评价“树梢挂蛇”与“石压虾蟆”,看似调谑,开怀大笑之余,“以为深中其病”,实际上也非常形象贴切地概括了二人的书法风格,可以看出师生二人滑稽善谑的相互评价是卓有见地的。
宋代士人治世报国的理想,在宋代笔记中也有生动丰富的记载。如《渑水燕谈录》载:“往年士大夫好讲水利。有言欲涸梁山泊以为农田者,或诘之曰:‘梁山泊,古钜野泽,广袤数百里。今若涸之,不幸秋夏之交行潦四集,诸水并入,何以受之?’贡父适在坐,徐曰:‘却于泊之傍凿一池,大小正同,则可受其水矣。’坐中皆绝倒,言者大惭沮。”对“言欲涸梁山泊以为农田者”逢迎巴结之辈,“大兴水利,急于见效”的王安石急于询问梁山泊之水的排放办法。刘攽“却于泊之傍凿一池,大小正同,则可受其水矣”,滑稽之语,劝诫醒豁,显现了宋代文人特有的生存智慧。
宋代笔记的谐谑风格,一方面是其中所载录的宋代文人谐趣滑稽的鲜活形象,构成了宋代笔记特征鲜明的主题内容之一,从而使宋代笔记在文体上先天带有了谐谑风格。宋代笔记撰者身处浓重的滑稽善谑的社会风气之中,自然也多撰滑稽善谑之事,宋代笔记是载录此类内容最适宜的文体形式。人物是笔记的重要话题之一,笔记条目式的书写方式最终也能聚群成象,展现人物主流的性格特征和审美风度。另一方面,宋代笔记文体特征渐趋成熟,笔记作者创作倾向鲜明。他们或插科打诨竞才逗趣,或乡间野老调笑取乐,或讽谏时政笑傲王侯,宋代笔记作者已经将“供谈笑、广见闻”的创作观念转化为一种创作自觉。从宋代笔记序言中可以看出撰者对创作倾向和风格的自我体认。如欧阳修《归田录·自序》:“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王得臣《麈史·序》:“故自师友之余论、宾僚之燕谈与耳目之所及,苟有所得,辄皆记之。”叶梦得《避暑录话·序》“泛语古今杂事,耳目所接,论说平生出处,及道老交亲戚之言,以为欢笑”,正文又重申此意:“士大夫作小说杂记所闻见,本以为游戏……”姚宽《西溪丛语·自叙》:“予以生平父兄师友,相与谈说履历见闻,疑误考证,积而渐富,有足采者。”从撰者自序,可以明晰感受到宋代笔记撰者对谐谑风格的自我体认。
再如《渑水燕谈录》,作者自序与同年进士满思复题语都明确了笔记创作的自觉追求与风格特征。《渑水燕谈录·序》:“闲接贤士大夫谈议有可取者,辄记之,久而得三百六十余事,私编之为十卷,蓄之中橐,以为南亩北窗、倚杖鼓腹之资,且用消阻志,遣余年耳。”对于“贤大夫谈谑”“辄记之”的重视态度,这也是宋代笔记多数撰者的创作态度。满思复题语:“前人记宾朋燕语以补史氏者多矣,岂特屑屑记录以为谈助而已哉?齐国王辟之圣涂,余同年进士也,从仕已来,每于燕闲得一嘉话辄录之。凡数百事,大抵进忠义,尊行节,不取怪诞无益之语,至于赋咏谈谑,虽若琐碎而皆有所发,读其书亦足知所存矣。”即使是“赋咏谈谑”“虽若琐碎”,但也是“皆有所发”的,这种评价反映出时人对于笔记谈谑纪事功能的肯定与认同。
一些笔记甚至专设谐谑,如《渑水燕谈录》“谈谑二十三事”,王得臣《麈史》“谐谑”,江少虞《事实类苑》分二十四门,“谈谐戏谑”占五卷,沈括《梦溪笔谈》“讥谑”,《能改斋漫录》“诙谐戏谑”等。
宋代笔记虽然篇幅短小,且多是条目式的只言片语,作者善谐创作倾向也能在跌宕性的情节、生动性的叙事和经典性的场景中得以实现。如《归田录》载:“石资政好谐谑,士大夫能道其语者甚多。尝因入朝,遇荆王迎授,东华门不得入,遂自左掖门入。有一朝士,好事语言,问石云:‘何为自左掖门入?’石方趁班,且走且答曰:‘只为大王迎授。’闻者无不大笑。”“遇荆王迎授,东华门不得入”之事,只能“自左掖门入”的石延年,对于好事者调谑嘲笑之言“何为自左掖门入”,“只为大王迎授”,原因和盘托出,但却并不明言迎授的主体,由有失脸面变为自抬身价,“且走且答”,一本正经、滑稽调笑、机智敏锐的形象跃然纸上。如《侯鲭录》载:“东坡在维扬,设客十余人,皆一时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芾为癫,愿质之。’坡云:‘吾从众。’坐客皆笑。”“酒半,元章忽起立云”,画面感极强,“世人皆以芾为癫,愿质之”,米元章的酒酣自嘲之态跃然纸上,而苏轼短短一句“吾从众”,不仅令“坐客皆笑”,也定格为宋代文人交游谐趣的经典画面和宋代笔记谐谑风格的显性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