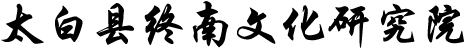一 序起
『大禹谟』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四句十六字,在中国固有文化中,是被称誉为道统、心传的。说到中国文化,从黄帝、尧、舜以来,经三代而凝定。这是重人事的,从人事而倾向于道(「志于道」)的。本于人,向于道的文化,是本着不偏不蔽的中道去实现的。人心、道心、执中,扼要的表达了中国文化的特质。这一特质,不仅是儒家的,也是道家的,说是儒、道、诸子所共同的,也没有什么不对。只是春秋以来,学术思想趋于自由,百家各有所重所偏而已。
有关人心、道心、执中的解说,『荀子』「解蔽篇」(解蔽,就是不蔽于一边而得乎中道),是现存较古的一种。如说:「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 …何谓衡?曰:道」。这是不偏蔽于一边,而衡以中道的意思。但怎样才能体道而中衡呢?『荀子』提出了:「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道?曰:虚壹而静。……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这是以虚(则入),壹(则尽),静(则察),为治心知道的方法。其后又说:「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之危,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机,惟(大清)明君子而后能知之」。『荀子』说到了「而中县衡」、「人心」、「道心」、「危」、「微」、「壹」、「精于道」,与『大禹谟』所说,显然有关。『大禹谟』是古典,还是「梅赜所釆窜」,虽然有待考证;也许舜时还没有如此圆熟的成语。但从『荀子』看来,「人心」与「道心」、「危」、「微」、「精」、「壹」,都是古已有之,不失为中华文化共通的特色。荀子的解说,在中国文化开展中,属于儒家,重于人道的一流。如从中国文化共同的根源(书、易、诗,都是古代传来的)而不同的开展来说,儒家以外,尽可有不同意趣的存在。
『大禹谟』为儒家所传,解说也都属于儒家。早期的『孔氏传』说:「危则难安,微则难明。故戒以精一,信执其中」。据此,精与一,属于达成执中的方法,与『荀子』说相同。朱子以人心为人欲,道心为天理,而执中为人欲净尽,天理流行。阳明以为:人心与道心,只是一心,而有真心与妄心的别异;这当然也归于尽妄存真。宋明理学──尽人欲而存天理,尽妄心而显真心,无疑是儒者深受当时的佛教,主要是禅宗的影响。然从老、庄、佛法、大乘正宗的空有二轮来看,应还有不同的解说。「危」是形容人心的;「微」、「精」、「一」是形容道心的。依人心以向道心,顺于道心,与道心相应,体见于道;体道见道而又不违(不碍)人心,这就是允执其中。这是本于人,志于道的进展过程中,所有恰到好处(中)的方针。孔子曾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智者与贤者,是重道的,而太过了,就会庄子那样的:「蔽于天(道)而不知人」(『荀子』说)。愚者与不肖者,每每是不及,拘于人事而不知有道。太过与不及,都是偏邪而非中正的。对人心与道心,不能正处中道,正是中国圣贤所慨叹,佛教圣贤所呵责的。在这中国文化复与的机运中,对人心与道心的中道,我愿略加论列,以祝赞中国文化,佛教文化的复兴。这不是为了立异,不是为了争是非,所以题为「别说」,聊备一解而已。
二 人心惟危
『大禹谟』的四句十六字,句读是可以这样的: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以「危」来形容人心,以「微」、「精」、「一」来形容道心。对人心与道心──二者,应该恰当的执其中道。因为,偏蔽于道,或拘执于人,都是一边,而不是中国圣贤所用的中道。
『荀子』「解蔽篇」,有「道人」与「不道人」,「可道之心」与「不可道之心」。依此来解说,「道心」是可道──合于道之心,也就是道人之心。「人心」是不可道──不合道之心,也就是不道人之心。这样,「人心」是一般人的心,「人同此心」的心。人欲,当然是人心,但人心并不限于人欲。如『孟子』说:「仁,人心也」。「仁也者,人也」。仁──仁义礼智,正是人心的重要内容。虽然从人(心本)性的立场,古人有性善,性恶,性善恶混等异说。然从现实的人心,人类心理现象去着眼,谁也不能否认,心是有善有不善的。人人如此的人心,的确是危而难安的。为物欲所陷溺,为私见所固蔽──「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那是不消说了。被称为性德的仁──仁、智、信,都不是完善的。所以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而且,仁义的阐扬,在人类历史中,多少也有些副作用。『庄子』「骈拇篇」说:「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又说:「三代以下,天下何其嚣嚣也!……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这所以老子有:「大道废,有仁义」的慨叹。总之,现实的人心,是在善恶消长的过程中。不善的会招致可悲的结果,善的也并不完善,并不彻底。人心的性质如此,的确是危而难安。所以古代圣贤,总是「居安思危」、「安不忘危」,而要从「修道」(修身以道)中,超越这危疑难安的困境。
三 人心惟危的辨析
人心所以危而难安,要从人心的辨析中去求了解。这在儒、道的著作中,是简略不备的。对于这,佛法有详密的说明,可以帮助了解「人心惟危」的问题所在。
人心(实通于一切众生心),是一般人的心理现象,心理活动。心,佛法或分别的称为「心」、「意」、「识」,与『大学』所说的「知」、「意」、「心」,非常类似,而内容不完全相同。依佛法,人类的心「识」,能了别(认识)对象──「境」;这要依于引发认识的机构──「根」,才能展现出来。如依眼根,而色(形色、显色)境为眼识所了别;依耳根,而声境为耳识所了别;依鼻根,而香(臭)境为鼻识所了别;依舌根,而味境为舌识所了别;依身根,而触境为身识所了别。这五识,是属于感官的知识。眼、耳、鼻、舌、身等五根,等于现代所说的视神经……触觉神经。还有依意根,而一切法境为意识所了别。意识所了别的,极为广泛。不仅了别当前──现在的,也通于过去的,及未来的。不仅了别具体的事物,也通于抽象的关系,法则,数量等。这是一般人所能自觉的,感官知识以外的认识。前五识与意识,总名为六识。意识(实在也是五识)所依的意根呢!这可说是过去的认识活动(或称之为「过去灭意」),而实是过去认识所累积,形成潜在于内的意(或称为「诸识和合名为一意」─「现在意」)。这是一般人所不易自觉的,却是一切──六识的根源。举例说(过去举波浪所依的大海水喻):六识如从山石中流出的泉水,而意根却如地下水源。地下水是一般所不见的,却是存在于地下深处的。地下水从何而来?这是从雨水,及水流浸润而潜存于地下的。意根也是这样,源于过去的认识,过去了,消失了,却转化为潜在于内的「细意识」。在大乘佛法中,更分别为末那识与阿赖耶识。过去意识(总括六识)所转化的,统一的,微细潜在的意根,在「人心」的了解中,极为重要!「人心」,不只是一般的五识与意识而已。
人心的活动,是极复杂的,融和的综合活动,称为「心聚」。不论前五识,意识,或内在的微细意,都有复杂的内容。其中最一般的,有三:1.「受」:这是在心境相关中,受影响而起的情感。如苦、乐、忧、喜等。苦与乐,是有关身体的,感官所直接引起的。喜与忧,是属于心理的;对感官的经验来说,是间接的。还有中庸、平和、安静的「舍受」,通于一切识。儒者所说,喜怒哀乐未发的境界,就是舍受的一类。2.「想」:这是在心境相关中,摄取境相而化为印象、概念。人类的「想」力特强,形成名言,而有明晰的思想知识。3.「思」:这是在心境相关中,应付境相,所发的主动的意志作用。从生于其心,到见于其事(语言或行为),都是思的作用。这三者,在心理学上,就是情、知、意。在人心中,心的一系列活动中,也有先受(感受)、次想(认了),而后思(采取应付的方法)的显著情形。但其实,每一念心,都同时具备这三者。也就是说,这是内心不能分离的作用。所以,佛法通常以「识」为人心的主要术语,而所说的识(六识或八识),却不只是认识的。
人心,是有善有恶的,而且是生来就有善恶功能的,所以说:「最初一念识,生得善,生得恶;善为无量善识本,恶为无量恶识本」。如加以分别,可以分为善、不善、无记(无记还可以分为二类),名为「三性」。不善中,以贪、瞋、痴、慢、疑,(不正)见──六类为根本。善中,以无贪(近于义),无瞋(近于仁),无痴(近于智)为根本。但有不能说是不善的,也不能说是善的,名为无记。无记,在佛法的解说中,是最精当的部分。善是道德的,不善是不道德的,这主要是与人伦道德有关的分类。如当前的所起一念心,没有善或不善的心理因素,也就是不能说是道德或不道德的(也就不会引起果报),那时的心── 心与心所,一切都为无记的。这不但一般的六识中有,细心(属于意)识的一类中也有。而内在的微细意中,从善不善心而转化来的,虽可说是善的潜能,不善的潜能,而在微细意中,却是极其微细,难于分别,只能说是无记的。所以说到人心深处,与「善恶混」说相近。但在混杂、混融如一中,善与不善的潜能,是别别存在,而不是混滥不分的。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虽说得简略,却与佛法所说相近。至于佛法所说的「心性本净」,那是一切众生所同的,是不局限于人伦道德的;不是一般善心──仁义礼智的含义可比!
不善的心所,名为「烦恼」,烦恼是烦动恼乱的意思。只要心中现起烦恼,无论是贪、是瞋……,都会使人内心热恼而不得安宁。进一步说,微细意中的微细烦恼,虽是无记性的,也有微细的热恼。如细烦恼发作起来,会使人莫明其妙的不安,引起情绪的不佳。所以危疑不安,在人心中,是极深刻的。这种微细意中的微细烦恼,是生来如此的(「生得」)。在前六识起麤显烦恼时,内在的细烦恼,当然存在;就是善心现起,细烦恼也一样的存在,一样的影响善心。所以人类的善心、善行,被称为有漏的,杂染的,并不是纯净的完善。微细意中的烦恼,佛法类别为四大类:自我的爱染,自我的执着,自我的高慢,自我的愚痴(迷惑)。概略的说:迷惑自己,不能如实的理解自己,是我痴。从自我的迷惑中,展为我爱──生命的爱染;我见──自我(神、灵)的执见;我慢──优越感,权力意欲。在微细意中,原是极微细的,一般人所不能明察的。但在佛教的圣者,深修定慧,反观自心而体会出来。扼要的说,「人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中心的心行,就是自心不安,世间不安的因素。例如布施、持戒,或从事于救国救世界的努力。在人类的道德、政治中,不能说不是出于善的。然在自我中心中,我能布施,我能持戒,不免自以为善。这样的人,越是行善,越觉得别人悭吝,破戒,而善与不善,也就严重的对立起来。不但自己的善心、善行,失去意义,而渐向于不善;对悭吝、破戒者,也失去「与人为善」的同化力量。「招仁义以挠天下」,引起副作用,也就是这样。在中国的汉、宋、明代,儒学昌明而引起党争,动不动称对方为「小人」;引起的恶劣结果,是怎样的使人失望!救人、救国、救世界,在自我中心中,会发展到:只有我才能救人救世;只有我这一套──主义、政策,才能救国救世界:世界陷入纠纷苦诤的悲惨局面,人心也就惶惶不可终日了!
人心,是情感、知识、意志的融和活动。人心的缺点,长处,都是通于这三者的。如情感的不正常;即使是正常的,受苦会使人恼乱,喜乐会使人忘形,而不知是刀头的蜜;不苦不乐的舍受,在流变过程中,不究竟,不自在,还是「行苦」。如知识,有正确也有谬误。正确是有时空局限性的,不宜固执,所以孟子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尤其是部分的正确,如执一概全,就陷于谬误,所以说「如盲摸象」。『荀子』「解蔽篇」所说的蔽,大抵是一隅之见。意志的自我性特强,可以善可以不善,而终于不得完善。知、情、意──三者,人心每不得其正,而又互相影响:这就难怪人心的开展,危而难安了!
人心,特别是人类的心,知、情、意──三者,都有高度的开展。经上说:人有三种特胜,不但胜于地狱、鬼、畜,也胜于天国的神。三特胜是:1.「梵行胜」:梵行是克己的净行,是道德的。依佛法,道德依慈悲为本,与仁为德本的意义相同。道德,是人类的特胜:一般地狱、鬼、畜(愈低级的,越是微昧不明),是生而如此,本能的爱,本能的残杀,难有道德意识的自觉。天国中也没有克己的德行,越崇高的越是没有。2.「忆念胜」:人类念力强,从长远的记忆中,累积经验,促成知识的非常发达,这是鬼、畜、天国所不及的。3.「勇猛胜」:人类为了某一目的,能忍受一切苦痛,困难,以非常的努力来达成。这在鬼、畜,与天神,是万万不及的。这三者,是人类情、知、意的特长。从好处说,这就是慈悲、智能、勇进。『中庸』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道也」。这是所以行道的三达德,与人类的三特胜相近。但依佛法说,知、仁、勇,都不就是尽善尽美的;在人心中,都不免有所蔽(参孔子所说的六言六蔽),也就都不免于危而难安的。
依佛法来说:「人心惟危」,要从五识中,也要从意识中;从恶心中,还要从善心中;要从情意中,还要从知识中;不但从麤显的六识,还要在一味的,微细的无记心中,深深去彻了才得! 四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如上所说,道心是「道人」之心,「可道之心」。这不是一般,而是希贤(人),希圣(人),以「至人」、「真人」、「神人」为理想,进而实现为贤人,圣人,至人,真人,神人──合于道的心。要说明道心,先要略明道的含义。
在中国文化中,「道」是百家所重的,所以古有一切学派,同出于道家的传说。在字义中,道是道路,与梵语的「末伽」相当。道路是前进所不可不遵循的;如「行不由径」,不但不能到达目的地,中途还不免遭遇危害。这种意义,被引申为人类居心、行事的轨律,如伦常之道,仁义之道,修齐治平之道;有普遍性与必然性,而为人生的常道。更引申为自然(天)──宇宙的轨律,道是宇宙的本体。到此,道就有了形而上的色釆了。在佛法中,与「法」──梵语达磨的意义相近。「法」是合理的,「非法」是不合理的,所以法是善的德行,及良善的习俗、仪则。法字引申为真理,「正法」、「妙法」,与「实相」、「真如」的意义相通。但在「法」的实践中,圣者们所有理智一如的内容,称为「法」,也就是「菩提」(觉)、「涅盘」(寂灭)。菩提是觉,但「正觉」、「无上觉」,决不同于一般的知,而是真理的体现。古人译菩提为道,是不无意义的(涅盘也不是客观真理,而表示实现真理所得解脱自在的当体)。玄奘译末伽为道(老子的道),而不许译为菩提,不免拘于文字了。然中国各家所说的道,内容不必尽同;与佛法的法、菩提、涅盘,当然也不相同。这里只表示在某一点上,意义有些类似而已。
在中国文化中,道有「天道」、「人道」。天道是自然的,人道是人为的。道家是重自然的,也就重于天道。『老子』说「天之道」,「人之道」,主张法天道以明人事。庄子更重于自然,所以『荀子』说他「蔽于天而不知人」。儒家是重人事的,也就是重于人道。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后人,都重于人道。而在阐明其本然牲,也称为天道,约人道约实践说。如『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也有此说)。总之,在各家中,都接触到天道与人道,而各就所重,予以发挥。在这人心与道心的对说中,人心是人道,道心是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