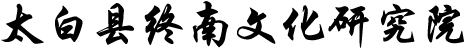篆刻艺术历史悠久,印人众多,概括地讲,篆刻史就是一部生动的“推陈出新”史。出新的风貌源于印人独特的理念。
晚明是篆刻艺术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此时,易于受刀、晶莹清润的青田石被广泛用于治印;顾从德辑《集古印谱》问世,为人们提供了经典学习范本。际遇交汇,使长久以来渴望刻印的文人群体有了亲历篆刻之乐的机会,刻印的热情如开闸之洪,为印坛开启明清篆刻流派朝气蓬勃的时代。
彼时篆刻风格最具代表性的印人,为文彭、何震、苏宣、朱简、汪关五大家。他们的理念是推倒中古、跨越中古,“印宗秦汉”。在篆刻流派的萌芽期,这种取法乎上的“复古运动”和“回归意识”,是必要的、有益的、合乎逻辑的。在“印宗秦汉”的共识下,一些印人亦推出新的理念与实践。青田石利于奏刀,何震便以直冲刀法治印,首创“刀笔兼得”的冲刀刻印及切刀刻款技法。朱简适应印石的切刀技法,则有别于何震的强冲式。这种避同求异,在“印宗秦汉”初生期,可谓新理念支撑下的创造。
明末清初,程邃出现。他意识到“印宗秦汉”的理念有其狭隘之处,于是以钟鼎款识入印,合大小篆为一,表现浑朴淳郁的气格,正是这种理念使其成为清初印坛巨匠。
高凤翰也是有新理念的印人。他破方正雕琢,求烂漫自在,其作汪洋恣肆,饶有狂放的醉意。
稍晚的丁敬,摆脱追踵秦汉或追求一家一派的局限,既师法周秦汉魏,又重视六朝隋唐宋元时期印章中可掇取的妙趣,对古今玺印作了全面梳理、学习、消化、借鉴,把“印内求印”的探索和成果推向极致。正是这一崭新理念,使他开创了面目一新、从者如云的浙派。
“新”一旦重复就失去了新鲜度,邓石如深晓此理。他洞察到“印内求印”已难出新意,提出“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新理念。浙派篆法尚方正,邓氏尚圆畅;浙派刀法尚切,邓氏刀法尚冲兼披;浙派及古来的印章,在篆法上少顿挫提按的节奏,而邓石如从汉碑篆额乃至汉人篆隶中,体悟到笔势、笔意、笔趣节奏起伏的特殊魅力,将其引入篆刻,真正使刀笔互换、互补,魅力倍增。刻印的疆域自此有了无限拓展的可能,客观上加快了篆刻艺术走向现代的步伐。
吴让之作为邓石如的传人,力求在“刻”上出新。自明末至邓石如,几乎所有大家的篆刻,都是深刻。吴让之却以“浅刻披冲”塑造了朴茂自在、婉畅虚灵的新印风。流派印章上百年,至吴让之,才有了“神游太虚,若无其事”的刀法创新。这是刀法走向现代的觉醒。
晚出于吴让之的钱松,亦尚浅刻,却与吴让之的技法迥异。钱氏以“短切碎披”的手段治印,似春蚕食桑,呈现悠然闲淡的拙厚静穆,追求“天真烂漫”的理念。
赵之谦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入印的文字视为创作表现的对象,并把金石、造像等消而化之,彰显于印中,因此,他的印风多姿多态。赵之谦主客观合一而多元的扩散性新理念,似可概括为“物我相融,印化众妙”。由此形成的“印外求印”、新意迭出的多元篆刻风貌,远远超出了邓石如“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范畴。
以往的创新理念,从气格上讲,大多“正襟危坐,斯文雅妍”。吴昌硕别具只眼地洞察到这一倾向,并以谦逊之心探索更前卫的理念。从封泥中,他窥出“刀拙而锋锐,貌古而神虚”的玄妙;从砖瓦中,他悟出“道在瓦甓”的哲学;从烂铜印中,他体味到朽烂是大自然对印章进行的“再创作”。这些新理念造就了吴昌硕,使他练出“做”印的独门功夫。他运用百般手段,使印残蚀、漫漶、凹凸、润燥、断续、离合……他“做”印,“做”出了秦汉碑碣历经岁月风霜而古意隽永的况味,“做”到了出神入化、个性凸显、别开生面。
黄士陵与吴昌硕同时,自幼即研读《说文》,一生荡漾在吉金贞石的长河里。因此,他有底气倡导“篆”当“合以古籀”的理念。在配篆的章法、字法的印化上,他于横线条间,制造细微参差的距离,甚至使其稍作斜欹,平实中见灵变。在“刻”上,他也有独到的审美理念,篆作呈现出持力强冲、华贵爽挺的光洁。
20世纪也是印人辈出、风格多元的世纪。从守正创新来看,齐白石是不可不论及的印人,他的“大写意”简约印风与绘画“衰年变法”的新理念,同时起步并取得大成。其篆刻舍圆就方,强化了单刀直冲的猛利霸悍。此外,他的配篆、印化,采用纵横交错、大开大合、别致而强烈的几何分割,去花哨、去婉约、去繁琐、去忸怩,不拿腔拿调,特别会调用疏密虚实的冲突及和谐,一如他的大写意画风。这也是多为前人所忽视的创新表现。
500年的篆刻创新史,其实是一部理念出新史。理念关系着作品的意趣、格调、情操、风貌,还孕育、统领着那千差万别、因人而异的高妙技巧。巨匠们的成功和成就表明,只有确立新的理念,才有奋斗的目标和力量,才有超越前人、与时俱进的可贵创造。回望印坛,500年来涌现的这些巨匠,无不重视、敬畏、借鉴前人积淀的优秀传统,又无不在此基础上自塑自立。他们以切身行动遵循着“推陈出新”的艺术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