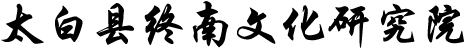在刚刚落幕的第二次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会议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司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吕忠梅从一个学者的视角,高度肯定了2015年11月福建上杭第一次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会议以来,环资审判工作取得的跨越式发展,认为绿色审判体系已基本形成,对中国特色的绿色审判道路充满信心,同时也提出了她对环资审判实践的一些学术思考。
不同审判庭都要树立绿色司法理念
首先,生态文明理念必须在所有的审判活动中加以贯彻,在目前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与普通化并行的格局下,如何在传统民事、刑事、行政审判过程中体现绿色审判原则?针对有地方出现的认为将传统案件放到环资庭审理,更容易认定合同无效的问题,吕忠梅认为值得警惕,不能简单以环境资源保护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而是不同的审判庭都要树立绿色司法的理念。
其次,环境案件中的新问题、新情况很多,法律制度供给不足。实际上,也不可能出现完全覆盖环境资源司法所需要的所有法律。吕忠梅强调,这就需要法官运用生态文明的理念对现行法律进行解释,通过对传统法律的绿色解释裁判新型案件,当然也必须遵循法律解释原则。
第三,环境司法需要创新,环境民事、行政审判权应当在可能的限度内融合发展。同时,环境问题不仅仅是技术事实问题,也涉及法律价值导向。目前案件审理中依然存在“鉴定为王”倾向,这是有问题的,应当将技术因素、社会价值综合考虑,以确定环境保护的限度。这里不仅有环境司法本身的问题,也有法官理念上的问题,吕忠梅指出法官要作价值判断,要做利益平衡,不是怎么鉴定怎么判。
环境刑事案件中科技证据该如何使用
第一,通过梳理环境刑事案件的裁判文书,吕忠梅发现法官对刑法第338条规定的污染环境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的理解不太一致,对此,学界也有争议。吕忠梅认为,行为犯和结果犯不是说只要刑法规定了结果就是结果犯,而是需要结合犯罪构造、侵害的法益进行综合考量。行为犯与结果犯对因果关系的证明要求是不同的,行为犯不需要证明因果关系,只要达到“两高”司法解释中规定的超标3倍、倾倒3吨等客观标准就可以定罪量刑,不需要再花费巨大的成本进行因果关系证明。
第二,科技证据使用问题。吕忠梅不反对科技证据的使用,通过科学鉴定等方式加强对案件事实的还原程度是当前环境司法的重要发展方向,但是,科技证据在不同类型的案件中的使用方式、使用限度存在差异,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在环境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可以使用科技证据来证明自己无罪或者罪轻而进行辩护,因为刑事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基于任何证据形式的法定辩护权。但是,对于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在科技证据使用上,则应该存在限度,证据达到公诉标准与审判标准即可,这是因为环境犯罪各种罪名的构造不同、证明标准也各不相同,法律规定了客观标准。
另外,科技证据的获得需要大量成本,这个成本也需要有限度。泰州水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掏鸟窝案等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些案件也充分说明,环境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证明要求是不一样的。在环境刑事案件中,科技证据的使用要有限度,不应该过度追求。
应细化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规则
吕忠梅提出了两个大的方面、若干具体问题。
一方面是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审理问题,包括受案范围如何确定?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是否需要履行前置公告程序、是否可以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要不要以穷尽行政执法救济为前提、是否可以根据检察机关要求举行庭前会议?还有,检察机关是否可以自行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如果检察机关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证据保全,败诉了怎么办?有些地方规定层报高院是否合理?检察长列席法院审委会讨论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是否合适?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检察机关如果不服,是向上级法院提起再审申请,还是向上级检察院提起申诉?或者上级检察机关直接对下级法院生效的民事公益诉讼裁判进行抗诉?提起再审申请以及抗诉的具体条件如何规范?
另一方面是关于诉前程序。诉前程序是检察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非常重要的制度创新。修订后的行诉法第25条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但不清楚具体程序构造与审查标准。
目前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矫正行政违法行为的功能是否应该体现在诉前程序中,目前采用以结果审查为主的标准,不利于这个功能的实现;二是规定两个月的履职期限问题,吕忠梅指出,这一规定没有考虑复种补绿需要时间、行政机关履职需要法定程序时间、部门联合执法需要协调时间等等,如果再采取结果审查标准,也会影响诉前程序功能的发挥。
对此,吕忠梅建议应进一步细化诉前程序和诉讼程序规则,将判断行政机关的履职标准从结果导向转为行为标准,将履职期限改为以两个月为原则,同时设定弹性空间的例外。
应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互补关系
吕忠梅首先解释,当前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法律属性有不同认识,她自己用了“国益诉讼”的概念,主要是为了与公益诉讼相区别。在司法实践中,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公益诉讼的衔接以及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的地位问题。
第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关系。实践中有三种理解:一是并列,将两者等同;二是区分主次,认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优先于社会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三是排斥,认为只要提起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就不能再提起公益诉讼。吕忠梅认为两者之间应该是互补关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实现《环境保护法》规定的损害担责原则的一种责任承担方式,不是对原有责任承担方式的替代,是对原有责任承担方式的补充,它们之间应该形成互补。
第二,关于检察机关如何参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问题。改革方案未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检察公益诉讼的衔接做出规定,仅规定最高检负责指导有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检察工作。改革方案对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仅设定了违反法律法规造成严重生态环境损害的条件,并未规定需以穷尽行政救济手段为前提。检察机关可否针对政府没有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行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如果检察机关在政府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过程中发现政府有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的情形,可否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如果政府已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检察机关可否再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吕忠梅建议最高法正在制定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司法解释中,应该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互补关系,并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民事诉讼、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作出衔接性安排。
环境资源审判已到向精细化发展的阶段
对于涉海洋诉讼中的一些新问题,吕忠梅注意到,一是已经发生的社会关注度高、也对海洋环境造成了损害的事件,比如桑吉轮爆炸、碳九泄漏等,没有进入司法程序;二是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原告起诉无序,索赔途径主次不分;三是今年机构改革后,负有海洋环境监管职责的行政机构名称、归属均发生变化,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原告主体需要尽快明确;四是陆源入海污染的管辖归属需要进一步明确;五是索赔范围的长期困扰。
当然,学术观察与审判实践存在一定距离。吕忠梅说,学术观察可以给法官一个新的视角,环境资源审判的很多机制正在形成中,学术理性对于机制的建立非常有价值。中国的环境资源审判已经到了向精细化发展的阶段,更应该及时总结裁判规律,形成理性认识。绿色审判不是只靠价值取向正确或者政治正确就能做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吕忠梅相信,在这次会议后中国的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一定能够迈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