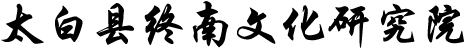这些年,打着城镇化和申遗的旗号,我们看到有大量古村落和文化遗产被毁,确实让人痛心。为申遗,拆除真正的文化遗产;为城镇化,消灭一个地方的文化与历史记忆。各地政府常说的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对文化误解最深的一句口号。把文化当作生财之道,把文化遗产当作立项圈地赚钱的噱头,是这句口号背后的真实含义。文化遗产不是那些造假的古建赝品,不是可胡编乱造的野史逸闻,它是弥漫于当地建筑与景观当中的一种内在文化精神,是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心灵状态。这种文化精神的形成是复杂而缓慢的,需要漫长的成长期。
有数据显示,30多年来中国的城镇化率已从18%提升到50%以上,城市人口增加了4亿人,在人类历史上,这种城市的大跃进从未有过。很多候鸟般的迁徙者,只能忍受着背井离乡的孤独,内心处于游牧状态。但很多城市与城镇,由于未注重对历史记忆和文脉的保存,城市成了钢筋水泥铸就的硬壳,困惑疏离、精神匮乏与心理焦虑成了很多居民的常态。这些城市难以给移居其中的人,以凝聚力和家园感,那些在城市中的孤独漫游,慢慢湮没了这些曾与古城、远山、炊烟产生和谐共振的心灵。
城市和文化遗产的关系不言而喻。所谓城市文化,核心是一个城市的文化遗产和历史记忆,那些著名城市也因它们独特的文化遗产而著名。说起古罗马,人们会想起那里的竞技场和帝国文化;说起古雅典,人们会说到那里的悲剧艺术和对自由价值的推崇。中国古代城市也是如此,盛唐长安开放而包容的文化气象,明清苏杭通俗文化的繁盛与隐逸文化的气质。一座城市如果能找到自己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个性,市民也就能共享这份集体记忆,它更能唤起市民对城市的文化认同。找到了历史和文化上的区别,也就找到了城市的形象;找到了市民的自豪和自信,也就找到了城市的活力。
从这些城市我们可看出,城市虽然是人们参与创造、构建而形成的居住地,但这种参与,并不意味着城市形态和结构可承受任何人主观意愿的干涉。我们今天居住的城市形态,大多是在并无整体规划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有着天然的历史记忆和大量文化遗产,它们并不是来自人们有意识的设计与规划。
如今,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规划,无法满足市民居住心理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规划往往缺少天然历史记忆,更没有文化遗产可言。虽然城市环境是人为创造的,但不意味着人类可依造蓝图创造一个新城市。前几年,我去的澳大利亚堪培拉就是一例。这是一个完全靠人工规划创造的城市,虽是澳洲首都,但一到周末或晚上,就成了一座毫无生气的空城。城市在“有历史感的创造”与“人为地强制规划”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在城市生态进化中,有创新与变革,也有后退与失败,没有人能真正控制这种进化体系的运行与发展,更没有人能决定它的进程。正如爱伦堡在谈到巴黎的奇妙时所说,它是像树林那样自然成长起来的,好的城市形态也如同自然界的有机体一样,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而无意识的历史进化。
城市也像植物一样,不能拔苗助长。城市在今天,不仅意味着要拥有摩天大厦和繁华市场,更应被看作是社会权利、历史文化最大限度的集中,它已成为文明的推手,将人类的文明经验不断演变为真实可感的符号。这种对城市多元性和独特性的认知,在当下内地仍是模糊的。
过去因狭隘的经济视角,在城镇化过程中,只关注钱财物,不但忽视了人与文化,更忽视了对社会公平、生态环境的关注。新一轮城镇化最重要的,首先是要还上这些历史欠债,才能真正化解那些积压太久的社会与城市问题。当城市建设和保护文化遗产遭遇矛盾时,城市建设显然应当让道,因为这些文化遗产和历史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没有“双赢”选择。而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本身,就蕴藏着经济机遇。只有保护了这些文化遗产,人类才有心灵和文化之根,经济发展才有意义。
城镇化是中国一个漫长时期的历史任务,它是庞大的经济工程和文化工程,更是一次深刻的社会结构与政治观念的变革。实现一个诗意的中国,显然不能只靠诗意的手段,而要动员全社会的智慧与力量、凝聚各阶层的共识、运用更权威的法律手段,才能让诗意成为可能。不急功近利,不拔苗助长,这是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