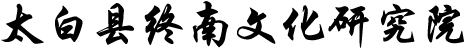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文艺工作者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史诗是人民创造的,不论多么宏大的创作,多么高的立意追求,都必须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从而深刻提炼生活、生动表达生活、全景展现生活。
任何时代,史诗从来都是文艺创作应有的最高追求,也是文学价值经典性的体现。在快节奏、娱乐化、碎片化的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往往不再追求史诗性,甚至以消解史诗性为前卫,取而代之的是专注于日常书写的“小长篇”。不可否认,小长篇中确有很多优秀作品,但也不乏为凑篇幅而以技巧拉伸或内容注水现象,以致出现评论者所说的“时代之重与写作之轻”的不对称感。纵观历史,能经得起淘洗和冲刷的流传之作,或气象宏阔,或精神深邃,它们构成了文明的精华和文化的经典。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作家、艺术家不能总是深居在书房里,不能总深陷在文本中,更不能脱离中华文化之根和远离丰富的民间生活。只有不断汲取传统与民间的源头活水,才能书写出高质量的史诗之作。 高尔基曾说:“各国伟大诗人的优秀作品都是取材于民间集体创作的宝藏,自古以来这个宝藏就曾提供了一切富于诗意的概括、一切有名的形象和典型。”的确,文学艺术中的优秀之作,都蕴含着丰厚的民族文化精髓,都是文化传统与民间文化的承载。民族性不仅是文学的重要精神资源,而且是身份徽标,是其独特性、创造性的体现。
民间文学资源是文艺创作的资源库、素材库,并给予创作以灵感和启示。从中国文学演进和嬗变过程看,很多文类与体裁的出现和繁荣,都可追溯到广阔的民间。如《离骚》《九歌》等作品与民间祭祀歌谣密不可分,传奇小说受到口耳相传的俗讲和变文的影响。而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大禹治水、嫦娥奔月、鹊桥相会等瑰丽的文化遗产,构成了中国人独有的创造与想象,也沉淀成为民族的原型意象与潜隐结构。
民间文学所蕴含的文化精神、思想内涵、美学价值乃至语言艺术,是民族文艺的立身之本、生机所在。别林斯基评价民间文化对于果戈理文学成就的意义时指出:“如此可爱的托名为养蜂人的果戈理,是一位非凡的天才。谁不知道他的《狄康卡近乡夜话》?这里面有多少机智、乐趣、诗意和人民性!”其实,果戈理的成功并非因为他具有什么“非凡的天才”,而是他植根于乌克兰民间文化沃土,体现的是民间文艺的伟大和丰饶。
很多优秀作家的成功也表征了民间文化的决定性作用。汪曾祺多次表达民间文化对于创作的意义:“我觉得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我们要‘以故为新’,从遗产中找出新的东西来……特别是民间文学,那真是一个宝库。我甚至可以武断地说,不读一点民歌和民间故事,是不能成为一个好小说家的。”贾平凹在谈创作体会时也强调作品要有现代性、传统性和民间性。莫言提出作家要“大踏步后退”到民族传统。他们的不少作品,深植于文化传统,浸润了民间滋养。
文艺创作与生活、时代的关系,永远是作家、艺术家要正视的第一要务。文学艺术要与时代同频共振,作家、艺术家要做时代的发现者和感知者,要用宏阔的视野、深邃的思想统摄时代的变迁、心灵的悸动,感应时代的召唤,完成为时代而歌、为人民抒怀的文学使命。
1991年5月,巴金在写给全国青年作家会议的贺词中说:要用心写作,将心交给读者。巴金的这句话,饱含他对文学和读者的深切挚爱,至今听来依然心潮澎湃。的确,要想创作出经典的史诗之作,需要创作的勇气、智慧和创造力,更需要真诚地思索、真诚地回归生活。文学创作不是纯粹的智力活动,不能脱离生活,应该力戒浮躁,一头扎入生活。故事可以编,生活不能编。路遥的文学道路对于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为了写《平凡的世界》这部长篇小说,他专门提前准备了两三年时间,深入生活,实地采访,观察各阶层人群的日常生活细节,翻阅报纸文献潜入历史,克服各种困难,忍受各种痛苦,孤独地行进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以热烈的情怀,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创作了当代文学的名篇巨著。《平凡的世界》出版以来,年年加印,经久不衰,至今仍在小说类图书畅销榜上名列前茅。路遥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动情而真诚地书写了时代变迁、不同人的命运及青年一代的人生奋斗,《平凡的世界》称得上是一部中国城乡社会改革的历史画卷和时代史诗。这部作品的成功,印证了歌德关于经典的民族作家产生的论述:“他在他的民族历史中碰上了伟大事件及其后果的幸运的有意义的统一;他在他的同胞的思想中抓住了伟大处,在他们的情感中抓住了深刻处,在他们的行动中抓住了坚强和融贯一致处;他自己完全被民族精神渗透了,由于内在的天才,自觉对过去和现在都能同情共鸣……”
一个时代文艺创作的高度,取决于优秀与经典之作的多寡。而优秀与经典之作取决于作家、艺术家的才华与追求。只有拿出“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耐得住寂寞与清苦才能创作出史诗性之作。眼下的文艺创作存在质与量之间的严重背离与不均衡。有人说,这是一个长篇狂欢的时代,一切似乎都以长为美,以快为佳。这不计其数的海量作品,能够成为经典的寥寥无几。有的作家不是几年创作一部长篇,而是一年写两三部,这当然与以利润思维碾压审美取向的商业逻辑和眼球经济直接相关,在靠频繁地“露脸”“出镜”来刷存在感的时代风气下,作家艺术家们唯恐自己被边缘化、被淡忘,不得不随波逐流。不讲质量,只讲数量,不求品位,只求长度,注定难以产生精品。
精品的打造和淬炼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做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缺少伟大的作品,没有史诗之作的产生,这不仅是文艺界的遗憾,也是时代的缺憾。要深刻认识到,史诗之作不仅是民族文化的柱石,也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撑。